 “一汀烟雨杏花寒”——中国古诗与杏的跨文化“旅行”.docx
“一汀烟雨杏花寒”——中国古诗与杏的跨文化“旅行”.docx
《“一汀烟雨杏花寒”——中国古诗与杏的跨文化“旅行”.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一汀烟雨杏花寒”——中国古诗与杏的跨文化“旅行”.docx(16页珍藏版)》请在第壹文秘上搜索。
1、“一汀烟雨杏花寒”中国古诗与杏的跨文化旅行梵高作品玻璃杯中盛开的杏花CAOXUEQINANDGAOETheStoryoftheStoneVo1.umeV霍克斯的红褛梦译本Rona1.dC.EganTheBurdenofFema1.eTa1.enthcPoct1.iQingzhaoandUcrHiSrOryinChina艾朗诺的才女之累ANI1.1.USTRATEDCOMPENDIUMofA1.1.thF1.own.Fn4t.HrWaTrco,idGrftMetCiredSi1.kWorMGrrimt力IPrr6I1.1.VtTftATVOSUM1.ftHSFGWACOEI.IXSVOBftVr
2、oiDBYHE1.ENM1.RRENGERITQyEA1.YBOTANICA1.SHAKESPEARE奎利的莎士比亚植物志荷兰画家阿德里安柯尔特作品五个杏子的静物暮春、初夏时节,正是“花褪我红青杏小”的时候。在这句词中,遇落的杏花与枝头的杏子标识了物候的变化,既细致地摹写了真实的景象,也表达了对人间春尽、时不我予的怅愧。红楼梦第五十八团“杏子照假风注虚凰,苗纱皆真情换痴理”,霜后初愈的宝玉见园里的“一株大杏树,花已全落,叶稠阴翠,上面已结了豆子大小的许多小杏”,便感慨病了几日,“把杏花辜负了,不觉巳到绿叶成荫子满枝了”。这里引用杜牧叹花中的诗句来表达光阴荏苒,美人也不免“鸟发如银,红原似镐后文
3、以雀儿见杏花开了又落而啼哭,周回曲折地描述宝玉的忧伤。杜牧诗后有一个凄美的故事:据说诗人早年伍识一女子,与其母约定十年后来娶,十四年后再逢,女子已掉为人妇:“待子十年不至,而后嫁之,三叔有子二人。”于是便写了此诗相赠。这里是用典,文中并未言明。不过,英国制译家友克斯的红楼梦译本中,将这一层意思明晰化了,把杜牧错失烟壕的传说写在了正文里.这一处理方式也显露了两种文化的差异。中国人见青杏挂枝,便想到都华易逝、红消香断,想到杜牧的“自恨寻芳到已迟”,以及诗后的传说。杏的指意如杏树的柔条一样,旁逸斜出,层层交错叠加。哀克斯也许觉得此处有太多的文化负载,需要一一剪裁、展开,才能彰显其中的恚义。莎士比业:
4、“提前”种下的杏树莎士比亚理查二世中也有描述园中杏树枝条旁生的段落,其中借园丁之口说道:“你去那边,把低垂的杏枝捆绑吊起,它们像无拘无束的孩子,用它们的重负,压弯了它们老父的躯体。把弯曲的枝干撑起来在我们的地盘里,这些枝条太高了,在我们的治理下,一切必须一般齐。”剧中将国事和花事联系在一起,以枝繁叶茂的花园来隐喻英格兰,用花园的疏于管理比喻王国的混乱。后世的论者多关注其中的隐喻,却较少谈及这里的中心角色一那些惹眼的杏枝。奎利(GeritQuea1.y)的莎士比亚植物志认为杏树是地道的中国植物,通过丝绸之路,经由欧洲大陆,在亨利八世时期辗转抵达英国,才开始在英国人的花园中落地生根。布拉克本-梅兹
5、(PeterB1.ackburne-Maze)的水果:一部图文史在经过考据后,也指出杏子起源于中国,“有可能直到15世纪中期才来到英国”。如此一来,理查二世的花园里便不可能出现杏树。就像袭力斯凯撒里的钟表一样,园中的杏树也同样是时代错乱的现象。英国有句谚语:荷马也有打的时候,指伟大的作家也有疏忽的地方。这里当然不是为了吹毛求疵,挑古人的错误。文学毕竟不同于历史书写,总会在现实中加上虚构和想象。杏还出现在莎士比亚的仲夏夜之梦中:仙后提泰尼妞吩咐仆从好好服侍自己的“心上人”:“恭恭敬敬地侍候这先生,蹿蹿跳跳地追随他前行:给他吃杏子、梅莓和桑槌,紫葡萄和无花果儿青青。”杏因其稀有而显得比寻常的水果更
6、加珍贵,作为表情达意的形象也更容易在看剧的观众中催生关于贵族生活的联想。杏是外来的物种,并未广泛种植,这一时期与杏相关的意象也只是零星地出现在文字之中,依然留存了诸多神秘的色彩。当时的博物学家认为食杏会导致消化不良,甚至流产。杏还是相对稀奇的东西。这大概是为什么帕尔特(RobertPa1.ter)研究文艺作品中水果书写的著作会以马尔菲公哥夫人的杏子以及文学中的其他水果(TheDuchessofMaIfi,sApricots,andOther1.iteraryFruits)为题,由此间接表露了杏与众不同的地位。这部著作的题名出自莎士比亚的同代人、剧作家韦伯斯特(JohnWebSter)的戏剧马尔
7、菲公爵夫人。剧中以杏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主要事物。杏被视作最先成熟的水果,其命名“apricot”的词根,也暗含了“早熟”之意,因而暗示了剧中人物珠胎暗结的情景。杏的花期早,惧怕霜冻的伤害,需要额外的照料,所以也显得更加娇贵。如布拉克本-梅兹所言,直到15世纪末,杏“还只种植在大型乡间别墅的花园里,在那里向阳墙壁可以为果树提供保护,以使它们茂盛生长”。宇文所安:杏林与杏坛关于杏花之早,中国古人早有认知,梅尧臣的初见杏花写道:“不待春风遍,烟林独早开。浅红欺醉粉,肯信有江梅。”意为春风尚未吹遍,万物还待复苏,林中杏花已独自绽放。戴叔伦的燕子不归春事晚,一汀烟雨杏花寒”,同样描绘了早春的景象。杏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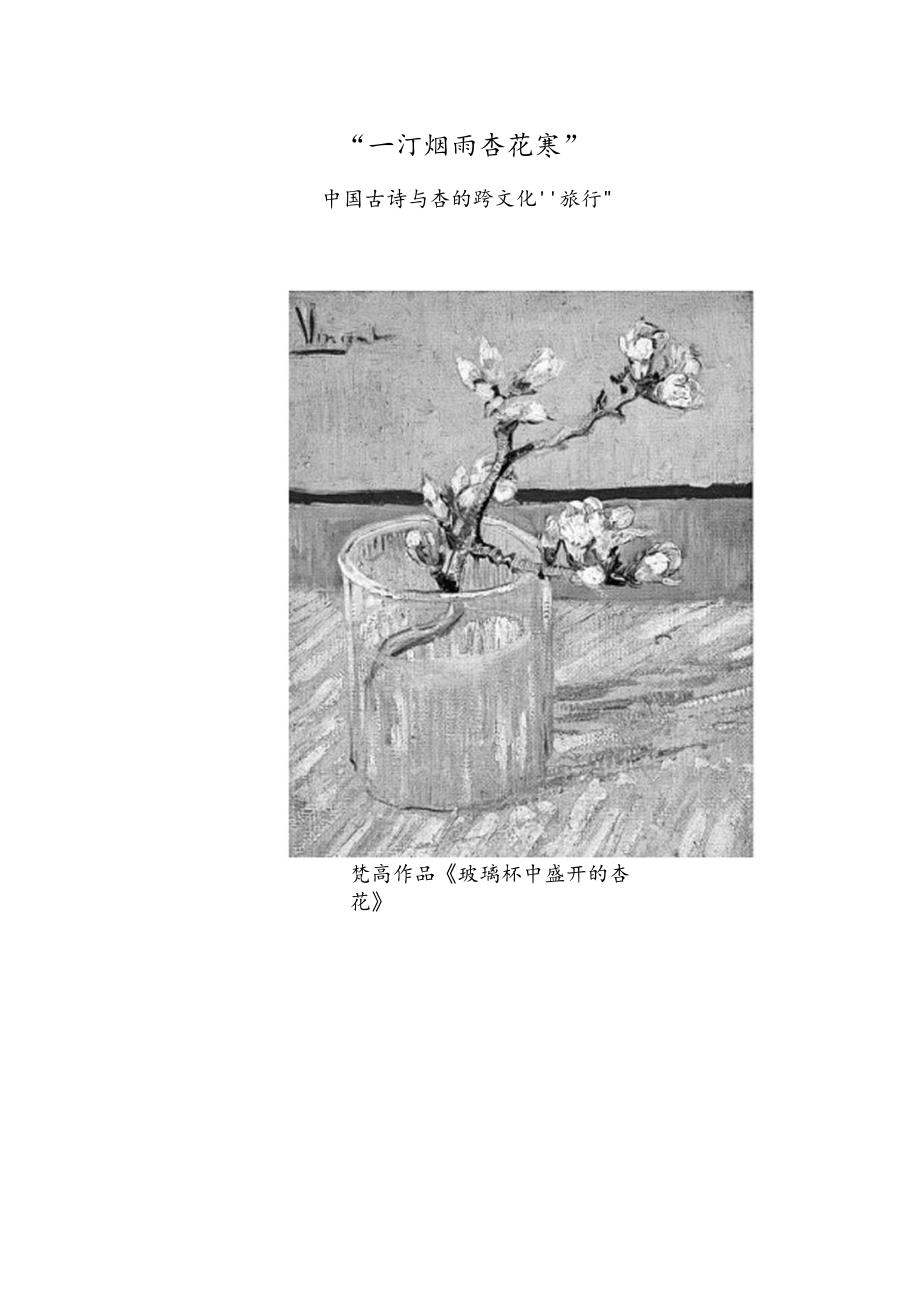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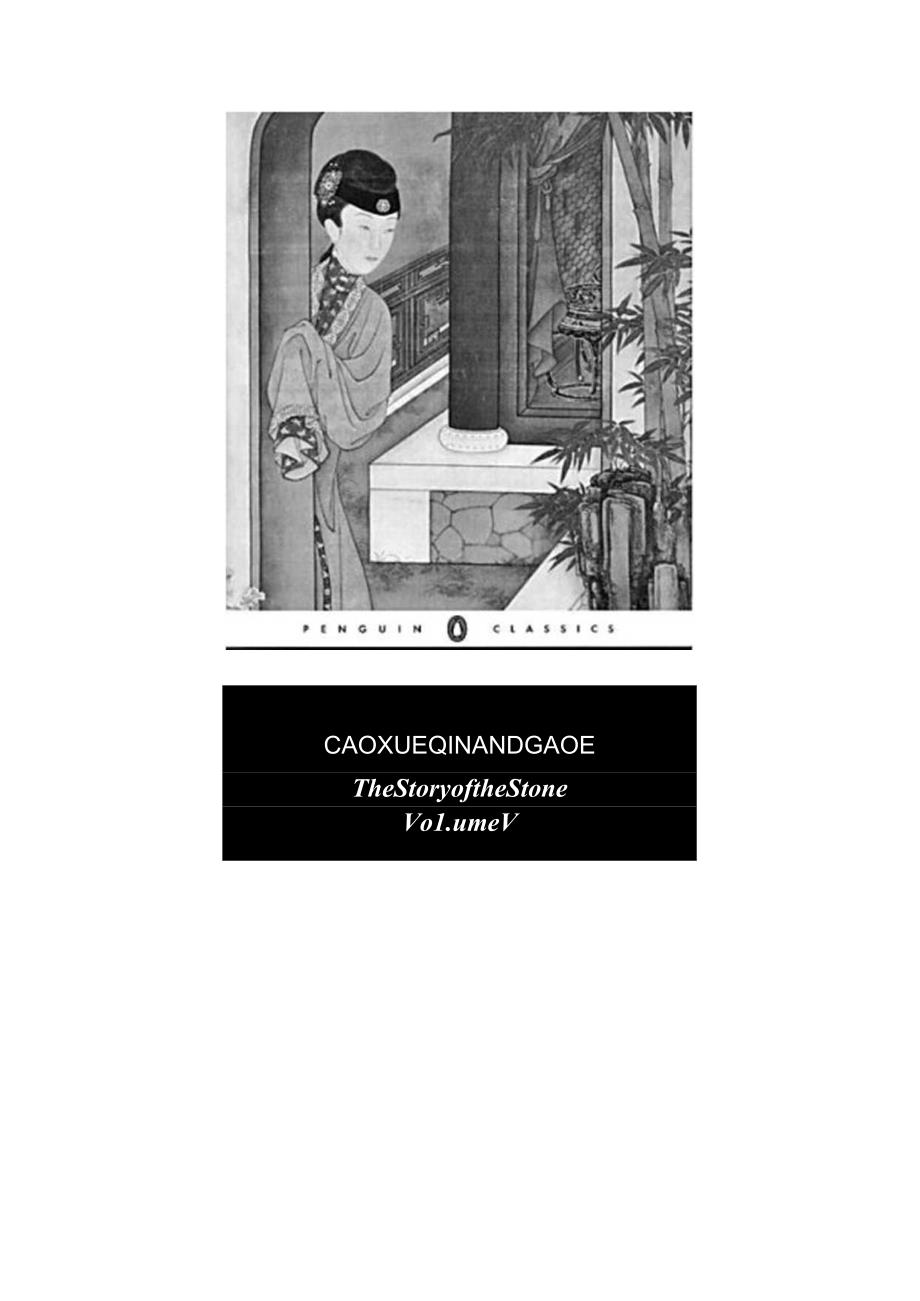

- 配套讲稿:
如PPT文件的首页显示word图标,表示该PPT已包含配套word讲稿。双击word图标可打开word文档。
- 特殊限制:
部分文档作品中含有的国旗、国徽等图片,仅作为作品整体效果示例展示,禁止商用。设计者仅对作品中独创性部分享有著作权。
- 关 键 词:
- 烟雨 杏花 中国 古诗 文化 旅行
 第壹文秘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第壹文秘所有资源均是用户自行上传分享,仅供网友学习交流,未经上传用户书面授权,请勿作他用。


 重点工作绩效评估自评表.docx
重点工作绩效评估自评表.docx
